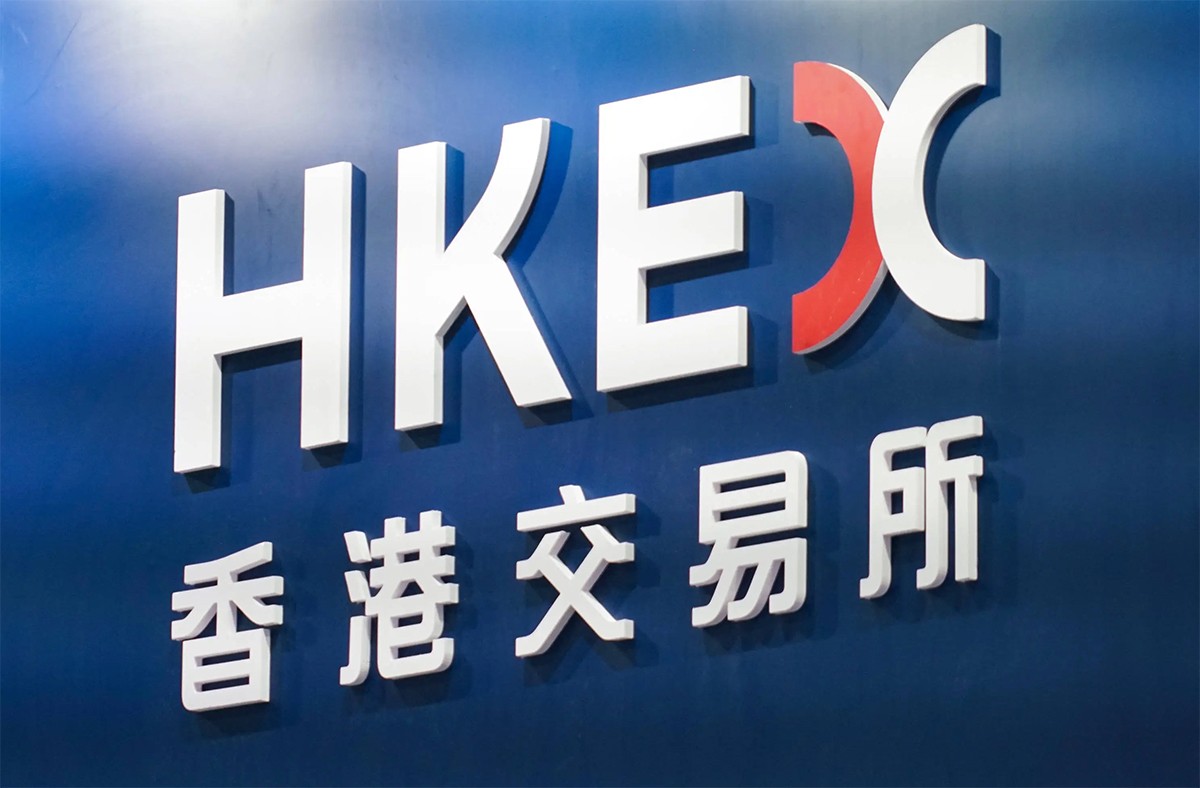资本的大小和经营理念决定一个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然而制药工业又是一个特殊行业,资本运作除了商业盈利以外还牵扯到社会责任、道德伦理等其它因素。所以本文从商业回报对比治病救人、研发创新对比“削减成本”两个方面来探讨现代制药工业的经营模式。
无法否认,在过去五十年里医药产业长盛不衰,商业回报也高于其它很多行业。产业链的每个部分几乎都表现出诱人的价值曲线,因而人们曾认为制药工业是永不落幕的朝阳产业。正因为此,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制药工业的商业回报和治病救人这两条曲线也基本重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默克CEO—乔治默克(George W.Merck)因此有一句名言,“我们应永远铭记,制药旨在救人……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
世界在变化,今天制药工业面临多重危机。绝大多数企业继续受到专利悬崖的冲击,新产品后继不足;监管门槛日益增高,和现有金标相比没有明显区分的产品已经不能受到监管和支付部门的认可;新药开发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相应地投资回报也越来越小,研发投入和商业回报渐渐不成比例,甚至很多人相信“新药研发是个亏本的买卖”,制药工业风光不再。这样,上世纪中叶辉瑞CEO约翰麦基恩(John McKeen)的经营理念“在人力范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所作的一切事情当中得到利润”开始越来越受到医药行业投资者的追捧。所以为了生存,今天的制药工业也在演变:新药研发渐趋多元化,经营模式进一步分化,真正能以创新药维持生计的企业越来越有限,在强调创新药研发的同时药厂以从来未有过的热情追求“削减成本”。
(一)创新药开发和“削减成本”的平衡
无论商业理念的差距有多大,药厂还是必须以制药为主,否则经营模式就出现了问题。所以现代制药工业的“削减成本”有其极限,这其中自然有象Valeant那样对“削减成本”的疯狂追求着,也有象基因泰克那样自主创新的典范。当然绝大多数药厂介于这两者之间,且在摸索达到创新和“削减成本”的平衡。这个平衡依赖于药监和支付政策的宽松程度、现有技术和主要尚未满足医疗需要的匹配程度、各国医疗资源的波动等宏观条件,Valeant和基因泰克哪个模式更有竞争力和上述环境的微妙变化直接相关。及时根据大环境调整资源配置、调整赌注是药企生存的必要条件,没有任何单一策略能在危机四伏的今天长期生存发展。下面笔者从最近的几单收购案的主角来点评这些公司的经营理念。
辉瑞收购阿斯利康案:
新药的来源无外乎两种,要么自主研发要么收购,后者又包括项目合作、公司收购以及收购期权(Option-to-Buy)等。辉瑞一度拥有超过年90亿美元的研发预算,但多年来产出却不尽人意,导致了自二十一世界初开始的一系列收购,其中包括以600亿美元对Pharmacia的收购(2003年)和680亿美元的惠氏并购(Wyeth,2009年),因此辉瑞也曾经变成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但是从收购获得产品线的一时“输血”并没有维持太久,立普妥失去专利保护以后年销售峰值从140亿美元跌至去年的23亿美元,虽然辉瑞也有靶向肺癌药物Xalkori和消炎药物Xeljanz的成功,但和因立普妥的损失相比有点杯水车薪。因此,2013年辉瑞的销售额从2012年的589亿美元跌至515亿美元。但是辉瑞的应对措施是进一步瘦身,并在创新和“削减成本”的平衡中进一步提高后者的比例,剥离了动物保健部门、出售了营养药物,以及大规模裁员。尤其重要的是为了裁减开支,和2012年相比,辉瑞的研发预算削减了11%,更从3年前的90亿美元降至2013年的66亿美元。因此,尽管辉瑞2013年的销售额降幅超过12%,依然保证了近5%的利润(见下图)。
信息来源:IMS市场研究所,其中运营结余指销售额剔除研发成本(R&D)、市场开支(Selling,General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SG&A)以及生产成本(Cost of Goods Sold,COGS)的结余资金。
收购案的另一主角阿斯利康则相反,在销售额大幅下降的同时把2013年的研发预算从前一年的42亿美元增至48亿美元,占当年销售额的19%。虽然阿斯利康近期的研发投入很难转化为晚期在研管线或产品,笔者也不信服其CEO宣称的9年销售翻翻的宏伟目标,至少说明阿斯利康开辟新产品的策略和辉瑞相反,以及向研发型药企转移的愿望和信心。正因为此,阿斯利康近期三度拒绝了辉瑞高达119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虽然节俭税收、获得免疫哨卡抑制剂的在研管线,以及上图所示的阿斯利康潜在的成本节约空间是辉瑞收购阿斯利康的直接原因,其实这次收购的真正幕后黑手是辉瑞对其内部新药研发的失望,以及希望持续通过收购来保证产品线的运营模式。
Valeant收购Allergan案
和辉瑞逐渐削减研发预算相比,加拿大最大的制药企业Valeant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Inc.根本就是反对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产品开发几乎完全依靠收购。自2010年以来,Valeant平均每年收购25个公司或项目,当然这些收购大部分很小且主要在高利润市场,自如皮肤科和眼科护理等。Valeant总部位于蒙特利尔(Montreal),原来是一家美国公司,在2010年9月被加拿大Biovail公司收购,并沿用Valeant名称以及J. Michael Pearson作为新公司的CEO。Valeant销售多种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医疗设备,医药产品主要包括神经内科、皮肤科和传染病,有几种新药已经上市如抗抑郁药Wellbutrin XL或在晚期临床开发。截至6月2日,Valeant公司的市值大约为440亿美元。
如果说Valeant还能被称为制药公司的话,那也是制药企业“削减成本”模式的极端表现。如果辉瑞收购阿斯利康一旦成功,裁员是一定的,但短期内至少保留研发的主要部分。而Valeant就不同了,将完全剔除收购公司的研发部分,这也是Allergan拒绝被Valeant收购的原因之一。自Michael Pearson从麦肯锡(McKinsey)跳槽来到这家公司担任CEO,就职伊始就指出“研发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行为”。Valeant采取纯商业模式运营:利用债务进行收购研发和产品,收购后大规模裁员,加强销售并在最大限度下地压榨运营成本获利。Pearson的纯管理理念受到很多投资人支持,其中包括Lou Simpson、Glenn Greenberg和Ruane Cunniff Goldfarb等着名投资人和投资基金。
事实上,这种纯商业经营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利润,而且不用担心不可预知的研发风险。三年内公司股票从2010年的十几美元飙升至6月2日的132美元,增幅近10倍。今年4月,Valeant联手投资大亨BillAckman准备以456亿美元收购以生产去皱药肉毒杆菌素(Botox)闻名的Allergan(艾尔建),若收购成功,Valeant将成为全球五大制药公司之一。5月底,Valeant进一步上调了收购艾尔建(Allergan)的要约价格,将整体价值提高至490亿美元以上,同时还调高了要约中现金部分的比例。此外,Valeant还承诺最多投资4亿美元继续开发DARPin眼药产品并额外提供每股25美元的价值权。但Allergan还是采取所谓毒丸计划(股东权益计划)来推迟Valeant的这次恶意收购。因为艾尔建的股东并不看好Valeant的“疯狂收购”商业模式。
Allergan(艾尔建)成立于1948年,是和Valeant相反的另类公司。Allergan商业上保守但注重研发,旗下10800员工中近五分之一属于研发部门。Allergan在2013年的研发投入达17%,在过去四年,艾尔建从FDA拿到了11个批文,且继续扩大神经系统产品肉毒杆菌(Botox)适应症。另一个药物,用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的Ozurdex也已经被批准,大量的糖尿病患病人群可以保证其巨额收入。
和Valeant相比,辉瑞在追求“削减成本”的同时结合了适当比例的创新药开发。其2013年研发投入和2012年相比降低了11%,依然远远高于Valeant,后者的研发投入仅占销售额的3%。辉瑞这次收购阿斯利康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不表明辉瑞的收购活动会因此而止。相反,因为辉瑞大规模收购的真正原因是公司内部研发效率低下,单靠自身的研发根本无法支撑销售的持续增长,辉瑞最终必须通过收购其它公司的在研管线来弥补自身研发效率的不足。如果研发产出不能高于投入,制药工业将无法持续,进一步的“削减成本”也只能加速整个工业的萎缩。阿斯利康在销售额急剧下滑的严峻情况下加大研发投入,信心值得敬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提高研发效率”的根本问题。6月2日,阿斯利康在2014年ASCO会议上公布了包括AZD9291、Olaparib等在研抗肿瘤药物的积极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之前Pascal Soriot表示的,至2023年阿斯利康年销售额达到450亿美元的宏伟计划,但计划的实施依然任重道远。
药源认为罗氏2009年收购基因泰克是制药工业至今最成功的案例。基因泰克(Genentech)由着名科学家、重组DNA的先驱Herbert Boyer和投资家Robert A. Swanson在1976年创建,运营模式以发现革命性新药为主,而且一直着保持创新这个公司文化。持续推出包括Rituxan(1997)、Herceptin(1998)、Xolair(2003)、Avastin(2004)、Tarceva(2004)、Perjeta(2012)、Kadcyla(2013)、Gazyva(2013)等明星产品。罗氏在2009年以468亿美元收购了基因泰克的剩余股份以来,且能够继续保持基因泰克的创新文化。正因为此,罗氏充沛的抗癌药产品线使其2013年的市场表现依然稳健,增长率达到6%。相应地也因为拥有相对丰富的产品组合和在研产品线,使得其管理层不必理会短期的利润追逐而专注于更为长远的业务规划的良性循环。尽管重磅炸弹药物赫赛汀和美罗华已经被仿制药虎视眈眈,最快明年,这两个药物的仿制药将上市,但是,基因泰克与百健艾迪一起研发的、美罗华的继任药物Gazyva已经于2013年获得FDA的批准,成为用于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一线用药,这将缓冲仿制药上市带来的冲击。罗氏仍然有66个新药在其研发线中,且15个已经进入后期研究阶段。
从以上三宗收购案主角的商业表现可以看出,创新药开发和“削减成本”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虽然如果每个药厂都采用Valeant模式制药工业会在20年内消失,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能容忍一两个Valeant式的企业。同理如果所有药厂都象基因泰克一样有创新力,制药工业无疑会再度成为朝阳行业,但是历史表明很多企业不能成为基因泰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特长追求一个合理的平衡,或者提高研发效率,或者提高资本效率。Valeant作为“疯狂收购”的代表,这种运营模式如果推广,虽然在短期内能进一步压榨医药产品的成本并提高利润,但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导致制药工业产品线的全面枯竭。实际上,Valeant的疯狂的收购已经为Valeant累计了170亿美元的债务,公司2014年需要“调整”经营性现金流(operating cash flow)达26亿美元。虽然公司股价持续上涨,但Valeant上季度的有机增长只有2%。Valeant虽然有近千种产品,但绝大部分都没有竞争力。尽管Valeant拥有更大规模的销售队伍,其二线产品Dysport的市场份额仅有14%,远远低于竞争者艾尔建Botox高达76%的市场份额。这充分证明,好的研发可以击败销售,好药比二线药需要的销售人员更少。不仅如此,Botox还有越来越多的适应症被批准,加速了艾尔建的有机增长。
(二)新药开发多种多样、经营业务日趋分化
综上所述,一个成功制药企业的经营模式必须达到“削减成本”和研发投入的平衡。而新药的开发,无论是内部研发还是外部收购,都必须依靠企业的研发投入。据GEN统计,全球前十名的制药企业在2013年对新药开发的投资额差距较大,介于11%至24%之间(见下表)。由于企业通常不透露用于新药研发(Drug Discovery)和临床开发(clinical development)之间的比例,难以评估每一个企业真正用于新药研究的预算。总的趋势是,和二十年前相比大部分制药巨头对研发的投入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商业回报却又明显下降。因为研发投入和经济回报的不成比例,很多企业在过去五年减少研发投资的比例。其中削减幅度最大的当属辉瑞,和2012年相比2013年的研发投入下降11%。也有一部分公司“顶风作案”,显着提高研发投入。增幅较大的包括塞尔基因(Celgene)和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分别为29%和21%。不过增幅的主要部分用于在研产品的临床开发。其中阿斯利康在销售额明显下降的同时和前一年相比依然增加13.7%的研发投入。持续把研发投入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制药巨头当属罗氏,2013年投入研发的预算高达99.1亿美元,占销售额的18.6%,仅稍低于五年前的19.4%。
除了研发投入在过去五年里增幅渐缓,另一个趋势是收购在研产品或公司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增高。对于大部分主要制药企业占一半以上。而且收购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其中包括收购企业、产品收购、合作开发、以及期权收购(Option-to-Buy)等。所谓期权收购顾名思义就是拥有一个收购期权。比如4月9日罗氏与Spero Therapeutics在抗生素领域达成合作协议,罗氏将对Spero提供研发资助,以此换取Spero在新的抗细菌感染疗法申报临床开发(IND)时优先收购的权限。这种期权收购模式的显着优点是大型制药企业在早期只需投入相对较少的资金,便可以享有在未来某一时间点以事先约定的条款收购整个公司或产品的权利。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现阶段的研发支出,另一方面又可锁定未来的潜在收益。近期发生的期权收购还有百健艾迪(Biogen Idec)—Ataxion、Takeda(武田)—Resolve Therapeutics、Novartis(诺华)—Sideris、Celgene(赛尔基因)—PharmAkea等。收购在研产品通常预先投入一笔较大的成本进行交易,但产品最终能否成为药品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合作开发在新药研发初期支付一定费用,后续根据里程碑事件付款支持药品的进一步开发,最终药品上市后拥有药品销售额的一定提成比例,这种模式属于风险共享,当然一旦成功利润也同样共享。企业收购同时也收购原有企业的成熟产品。过去十多年来医药行业的大并购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如罗氏收购基因泰克等。
和新药研发的多样化模式相反,制药巨头临床开发和产品经营的特点却趋向单一化。厂家开始专注于各自的经营强项。比如5月初,诺华、葛兰素和礼来等三个国际巨头交换价值250亿美元的资产:诺华出资160亿美元收购葛兰素的抗癌药部门,葛兰素耗资71亿美元换取诺华的疫苗部门,二者又合作成立了合资公司经营医疗消费品,诺华将其兽药部门以54亿美元卖给礼来。此次产品的大改组,一方面反映了产品收购也是新药的重要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制药企业生存环境日趋艰难。即使大如诺华、葛兰素史克那样的大集团,以及每年高达9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也不得不集中精力做自己擅长的业务。当然改组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研发效率,在特长领域获得规模优势,进一步优化在今天的苛刻环境下持续发现真正有价值新药的技能。
除了新药开发趋于单一化以外,现代制药产品的经营模式也向两极分化。比如尽管诸如Valeant这样的“削减成本”型企业被传统制药工业所不齿,但在今后的较长时间内依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虽然这些公司无法发现革命性的新药物,甚至也无法收购象样的高质产品,但他们的强项在于产品的选择,包括那些因为太小而不足以引起仿制药公司注意力的小产品、新剂型等,这些产品虽然不是明星但也能在短期内带来高额利润。总之,要在现代制药工业的竞争赛场中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找到自己有一定机会取胜的领地。
(三)新药发现多元化,临床开发份额增加
虽然缺乏制药企业用于新药研究和临床开发预算比例的全面数据,总的趋势是大多数企业逐渐增加临床开发的份额。所以尽管表1数据显示,大部分公司研发预算保持持续增长或稳定,但实际用于新药研究的开支却有所下降,而同时又要保障产出的增长,所以只能进一步压榨研发部门,在最节约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发现更多的高质量新分子实体。愿望是好的,但现在制药工业按照目前的科技发展状况,尤其仅靠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再加上市场监管和支付部门对药品质量期望值的提高,现在制药业的产出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明显下降。根据Goldman Sachs最近挑选的全球免疫/肿瘤类类前10位的大产品和20个处于中晚期有潜力的临床开发产品中,近75%的产品是通过非内部研发而产生的。Thomson Reuters等也统计了2010至2013年间跨国公司拥有的晚期临床阶段以及上市的创新产品也有63%来源于外部,这包括22%来自于收购、28%来自合资或共同开发、以及13%来自于授权。这些在研管线或产品的相当一部分最初甚至来源于一些不知名的研究机构或者小公司。
所以现代制药工业创新药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这既有效地利用了大学、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和丰富的创造力,也利用了政府资助的优势,而且很多小的生物制药公司最初的研究也来自于大学且经济上得到过政府资金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新药发现的成本通常低于大制药公司内部研发。在这些“大胆设想”发现新型新分子实体之外,大的制药集团越来越注重“小心求证”。这既包括通过临床开发论证新分子靶点对治疗疾病的有效性,也包括评价创新药在特定患者群的疗效和安全性。
现代医药工业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公共医疗的保健费用尤其在美国一直处在极高的水平,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保障机构已经不堪重负,无法承受更大的支出。所以医药工业基本上处于保证消费总额相等的同时趋向追求格局的变化。开发那些象Sovaldi那样的优质产品,取代一些鸡肋产品。比如礼来的ramucirumab虽然在今年四月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胃癌,但在这个星期的ASCO会议上报道,其非小细胞癌症的三期临床仅能延长不到两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很难让人相信这值得每个疗程可达90000美元的预期价格。Ramucirumab甚至被福布斯分析家Matthew Herper认为是本次ASCO最失败的临床开发之一。
总之,全球医药产业的严峻现状导致药厂既要“削减成本”,也要开足马力创新。短期内虽然制药工业依然有继续压榨的空间,但高品质/高药价的支付模式加上医疗花费总量相对恒定的现实决定了价值平庸的药物将逐渐被淘汰。尽管新药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审批和支付门槛的提高还是导致了新药研发成功率的下降,在多数情况下现在的技术条件我们无法根据临床前数据准确预测临床表现。除非我们对疾病的理解有质的改善,药厂必须继续扩大筛选空间,更多地依托外部资源发现候选药物。对药品创新性的更高要求也进一步加重了临床研究的负担,大制药公司可能被迫继续追加临床开发的预算。药物的质量越来越显得重要,有限的医疗预算会被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药品所瓜分。制药工业正在深刻分化,每个公司需要选择自己擅长的商业模式和疾病领域。大公司需要更依赖学校、研究所、小公司更广泛地寻找创新项目,而小公司和高校则要更多依赖大药厂的抗风险能力和雄厚资本完成新药的后期开发。在革命性技术出现之前制药工业还会继续萎缩,只有专注自己的强项,发现有一定机会取胜领域的药厂才能在这个优胜劣汰的残酷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来源:美中药源
为你推荐
 资讯
资讯 华东医药全球首个卵巢癌ADC爱拉赫®补充申请获受理
申报适应症为用于既往接受过1-3线系统性治疗的叶酸受体α(FRα)阳性的铂类耐药的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成年患者。
2025-03-10 19:36
 资讯
资讯 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辉瑞靶向免疫疗法易瑞欧(埃纳妥单抗)在华获批
今日(3月10日),辉瑞公司宣布,靶向免疫疗法易瑞欧®(埃纳妥单抗)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适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三线治疗(包括一种蛋白酶体抑制剂、一种免疫调节剂...
2025-03-10 12:07
 资讯
资讯 一款国产肺癌创新药头对头击败奥希替尼
日前,同源康医药发布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第三代EGFR抑制剂TY-9591(商品名:卡达沙)在对比奥希替尼(商品名:泰瑞沙)作为一线治疗EGFR突变肺癌脑转移的关键II期临床试验中,...
2025-03-10 10:55
 资讯
资讯 “AI+创新药”第一股云顶新耀开拓mRNA肿瘤治疗性疫苗新蓝海,在国内推进至临床阶段
近年来,AI 赋能创新药研发已成为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重要趋势,尤其在 mRNA 疫苗领域,AI 更是成为提升研发效率与精准度的核心驱动力。港股创新药企云顶新耀(HKEX 01952 ...
2025-03-10 09:29
 资讯
资讯 “全力治愈的春天音乐会”乳腺癌公益项目在南京暖心启航
3月7日,南京国民小剧场内,一场特殊的“疗愈音乐会”正在温暖上演。没有冰冷的医学术语,没有沉重的疾病阴霾,取而代之的是歌声、琴声、孩童的欢笑和患者含泪的拥抱。
2025-03-08 18:03
 资讯
资讯 部分企业未按要求上传价格承诺函被暂停相关产品采购资格
近日,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发布通知,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文件,因部分企业未按要求上传价格承诺函,即日起暂停部分别嘌醇片采购资格。
2025-03-08 10:19
 资讯
资讯 CDE:患者报告结局指标(PROs)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临床试验的技术指导原则
患者报告结局( 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 PROs) 是指任何来自患者直接报告但不包括他人引申解读的对自身疾病和相应治疗感受的评估结局。 该理念对临床上症状复杂、反...
2025-03-07 21:51
 资讯
资讯 国内首款,瑞龙外科分体式手术机器人海山一获批上市
昨日(3月6日),瑞龙外科在其官微宣布,其自主研发的海山一腔镜手术机器人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253010500),不仅成为了国内上市的首款分体式腔镜...
2025-03-07 15:18
 资讯
资讯 无锡发布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在锡医疗机构使用经认定的无锡产创新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等产品,不纳入医疗机构药占比和耗占比的考核范围。对创新药品、新批准注册药品和纳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2025-03-06 18:45
 资讯
资讯 罗氏制药中国携手京东健康赋能流感防治健康生态
今日(3月6日),罗氏制药中国与京东健康正式签署《流感防治生态共建深度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流感防治领域的长期深化合作正式启动。此次合作将通过整合双方优势资源,依托...
2025-03-06 16:25
 资讯
资讯 诺和诺德计划在线药房半价销售减肥药司美格鲁肽
日前,诺和诺德表示,将通过一家新设立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在线药房——诺和关怀(NovoCare),以大幅低于正常价格的费用提供其畅销减肥药司美格鲁肽(Wegovy)。这一举措旨在让...
2025-03-06 12:20
 资讯
资讯 华东医药Sinclair欣可丽美学光学射频治疗仪V30注册申请获受理
V30是Sinclair的全资子公司Viora开发的集射频(RF)、强脉冲光(IPL)、Nd:YAG激光能量源为一体的医美多功能操作平台
2025-03-05 19:26
 资讯
资讯 坚守女性健康承诺,欧加隆多维度投资“她未来”
2025年3月8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全球领先女性健康企业欧加隆重申志在革新女性健康发展蓝图的企业愿景。
2025-03-05 15:30
 资讯
资讯 荣灿生物HPV治疗性mRNA疫苗获得FDA临床许可
近日,荣灿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灿生物”)自主研发的人乳头瘤病毒(HPV)治疗性mRNA疫苗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临床试验许可。该疫苗的...
2025-03-05 07:34
 资讯
资讯 一款国产重磅ADC药物上市申请延迟
近日,据国家药监局政务服务门户官网信息显示,乐普生物的重磅新药维贝柯妥塔单抗(MRG003)收到“药品通知件”。根据国内现行的新药审批流程,如果药物顺利获批,则会收到“药...
2025-03-05 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