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学东渐”风潮迭起,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深入,与中医展开交流碰撞。起初双方尚能仅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甚至互相学习融通,至1912年民国始立,政治制度百废待兴,中西医的地位逐渐出现了不平衡。西医逐步进入官方的医疗行政管理系统,而中医界的反应则显得极为被动,往往是面临危险时才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于1931年,第一个将中医与政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机构——中央国医馆,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作为当时中医界的“最高”机构,中央国医馆的权责范围是什么?它的存在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中央国医馆的诞生
回顾中西医论争史,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的“旧医登记案”(或称“废止中医案”)最为人熟知。此案甫一公布,即引起了中医界一片哗然,上海市中医药团体率先在《申报》刊登启事,要求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大会议定具体办法以应对。大会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顺利召开。议决成立全国性质的医药团体——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其作为全国中医药界的“最高组织”,在领导中医抗争请愿、对外发声的同时,组织讨论决议,指导中医药发展,成为日后推动中央国医馆成立的重要力量。
全总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便是晋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撤消中央卫生会议的“旧医登记案”等,承认中医的合法性。请愿团拜访了谭延闿、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认为目的达到,安心返回了上海。
然而,出乎中医界意料的是,这次请愿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很快又先后颁布公告,对中医进行限制,可见请愿并无实质性效果。与此同时,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逐渐受到政府质疑。1929年8月,全总会向国民政府卫生部呈请批准立案,卫生部以全总会名称、会章存在问题等为由并未执行行政院准予备案的训令,将呈文搁置。全总会未取得合法地位,直至国医馆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其撤销。
几次请愿却没有实际效果、呈请政府立案却被搁置,还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这些因素促使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中医药管理权、合法性的争取上,希望仿照国术馆,建立有官方授权的“中央国医馆”,切实掌握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宜之权。他们很快向政府提交了提案,同全总会申请立案过程相似,国民政府文官处训令卫生部核办国医馆。卫生部则回复称国医馆简章所列的管理国医国药事宜属于行政职责,不在学术团体研究范围之内,应该删除。同时用提案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合法性问题对其进行根本上的否认,态度颇为消极。而行政院将其意见转请国民政府后,不再过问此案。全总会对于建设中央国医馆的提案再次被卫生部束之高阁,未获通过。
1930年5月,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上再次提出设立中央国医馆,获得原则通过,交由政府拟定具体办法,中央国医馆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几经延期,中央国医馆最终于1931年3月17日召开大会宣告成立。
二、中央国医馆的运行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很快便选举、确定焦易堂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任副馆长。在他们的主持下,1931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通过国民政府审核,这一章程列举了中央国医馆聘请医药专家设立专门委员会;附设医院、医药学校;组织管理各省市国医分馆;奖励有贡献的医药专家等工作计划,几乎包含了中医发展的各个方面:学术研究、现实应用传播、教授传承、管理联络。可以想见,若是能够按照这份章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中医应能得到良好的发展,那么真正的实践到底如何呢?
(一)整理、研究中医学术
由《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第一条所言中央国医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可知,中医科学化是国医馆众项工作中的重点。整理工作被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第二期为根据第一期审订的“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疾病名词;第三期则以前两期的工作成果为基础撰写全国中医药教材,并订正旧有中医药书籍。三步层层递进,最终目的即为谋求日后中医学术发展的一致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发展出“科学化”的“标准中医”。
在具体工作中,第一期工作较为顺利,而第二期工作,由于起初的起草人施今墨认为统一病名应以西医病名为最终依据。在发表后被指责不使用中医病名就是对中医的摒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即使更换了编审委员后,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不过国医馆之后并无动作,统一病名一项也就此草草结束。接下来第三期工作,虽在前期有征集中医书籍的广告,国医馆却并没有如期编审完成,只是检阅市面上流行的教材编成参考书单供教学使用,故也未取得较大进展。
(二)附设医院、发展中医教育
组织章程中附设医院及医药学校一项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在地方,以湖北省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指令公函为例。中央国医馆虽已下令准予备案,但还不到半个月,面对湖北国医分馆附设医院的合法性以及受何机关管理的问题,国医馆就又下发了此时尚未取得附设医院的管理权,仅有名义上的“监督”一说,医院筹设还需要内政部、地方政府的批准及管理之意的训令。
中央方面,1935年底,就有于右任、陈立夫、焦易堂等人为筹建首都国医院宴请多位中央要人的报导。此后四处募捐筹款,1937年初招标动工。不过,首都国医院尚未竣工,国医馆就因为抗战爆发,随政府撤至大后方,医院也未能真正建成。
那么医药教育情况如何呢?
自1929年教育部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后,1932年行政院再次下令要求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的附设中医学校,也须修正为学社。对于此令,国医馆并未进行反抗,这引发了中医界的极大反对,认为国医馆不争取中医权利反替教卫两部办事,训令最终并未贯彻落实。
1937年2月,焦易堂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议请教育部将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获得通过。可惜的是通过后尚未及时制定详细规章制度,国医馆就因为日军的威胁被迫迁至重庆,提案的执行受到耽搁。
(三)争取中医药管理权
中医药管理权本不在《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中,然而梳理国医馆工作,却发现其在此用力颇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即为促成《中医条例》的颁布。实际上,在最初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拟定的国医馆简章中,“管理国医药事宜”与“改进国医”、“研究国药”并列为国医馆所辖工作范围。只是在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时,卫生部将此条撤去。由于未被授予中医药管理权,中央国医馆在实际工作中屡受限制,始终不能很好地争取中医权利。因此1933年6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石瑛、陈立夫等二十九位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提交了《国医条例草案》。草案最终决议通过,交由内政部、教育部进行审议。
内教两部坚持认为国医馆是学术团体,并非行政机关,没有拟定条例的必要,决议将其修正通过,送交中央政治会议。7月,提案与行政院所附意见交立法院审议,立法院议决将草案交付法制委员会审查。此时身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在审议之前,走访了各委员,向他们解释《国医条例》的重要性,从而使草案顺利获得通过。最终,1933年12月立法院通过了《国医条例》,并将其改名为《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虽获立法院通过,但由于行政院的阻挠,迟迟未获得公布。其间各中医团体纷纷上书请愿。1935年11月,冯玉祥、石瑛等人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要求将《国医条例》公布实施,议决通过。几经波折,1月22日,《中医条例》正式公布。中医的合法地位得到基本确立。
(四)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央国医馆
上述工作多在抗战爆发前进行,1937年后,中央国医馆迁至重庆,抗战时期主要工作重心是配合政府,为服务军队、后方抗战民众等作了很大贡献。
1946年,中央国医馆复员回到南京。此后两年,尚未开展实质性工作,即因国民党迁至台湾而解散,其工作也就至此宣告结束。
三、多重视野下的中央国医馆
通过上文对中央国医馆运行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医馆的一些想法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个中缘由不仅有中医对于“科学化”问题的争论,更有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抵牾。
(一)政界视野中的中央国医馆
在国医馆运行期间,实际工作中一直伴随着发起者焦易堂等人与行政院对于中医药管理权的纠葛,两方针锋相对又妥协退让,我们或可猜测,中央国医馆成立运行的背后,有着国民政府内部的诸多博弈。
1929年“旧医登记案”提出时,正值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之时,其心腹褚民谊的提案在中医团体请愿时被国民党元老反对,背后的原因固然有元老们个人对中西医的偏好。此外,廖仲恺案后,国民党元老与汪精卫产生隔阂,面对褚民谊提出的如此有争议的提案,他们公开反对,对其进行打压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根基深厚,其向日本学习“废除汉医”、追求科学以变革发展的思想以及其培植的势力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蒋介石与元老们之间本质还是相互利用,甚至偶尔相互打压的权力利益关系。故在请愿后不久,教卫两部再度先后颁布了限制中医的公告。与“限制令”对应,中医界再次晋京请愿,获得了蒋介石借用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挥光大”遗训的批示。支持中医与追随总理的联系变得更加明确、紧密,元老们更是顺势借助此力量维护中医。于是就有了上文谭延闿、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提出设立掌握中医药管理权的中央国医馆一幕。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召开方为汪精卫、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势力联合反蒋,发动中原大战之时,不知是对汪精卫废止中医派所掌控的卫生部做出妥协,还是为了尽快推动中央国医馆通过卫生部审查的权益之计,在谭延闿等人提交的设立国医馆的提案中,除“兹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一句外,在详细的工作、组织大纲中均未提到授予国医馆管理中医药权的相关内容。1930年8月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公布之时,也就没有“管理中医药工作”一项的体现,最终导致了国医馆职能的尴尬。
中央国医馆正式开展工作后,中医药管理权缺失带来的掣肘促使石瑛、焦易堂等人于1933年6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制定《国医条例》,切实保证中央国医馆管理中医药的权力。对此,汪精卫在会上坚决反对,教卫两部也都未予通过。之后如上文所言,焦易堂各处拜访,推动了草案的通过,里面提到的国医馆管理权却被转给了内政部,“国医条例”也被改成了“中医条例”。
此期间正是汪蒋合流时期,双方虽都有争权,却也相互妥协。《中医条例》通过,一方面承认了中医的合法性,满足陈立夫、焦易堂等支持中医派诉求;一方面却又将中医管理权交给了内政部,并将带有民族性的“国医”还原为“中医”,迎合汪精卫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双方可谓各让一步。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中央国医馆自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等人将其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时开始,就已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派系斗争的工具。追求科学主义的汪精卫一方,欲以国家进步来获得权力认同;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元老一方,则希望标榜自身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来掌控国民政府。而蒋介石在整个过程中并无非常明确的指示,不难猜测中央国医馆是他用来制衡汪精卫一派与国民党元老一派的棋子,在双方互相争权打击对方时,坐收渔翁之利。中央国医馆是否能掌握中医药管理权,即在于汪精卫派、元老派及蒋介石三方的分合倾向,其地位、工作权限的变化又反映着各派系的起伏离合。
(二)中医内部对中央国医馆的争论
阅读国医馆成立时的诸篇评论文章,我们发现中医大都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是政府层面对中医支持的表现,同时,也有不少中医发出提醒,告诫同仁不要因此就依赖政府,放松对中医的研究。此外,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认为中央国医馆成立后能整理弘扬中医,使之能够进行“科学化”的改进,符合时代潮流,更好地发展,是中医界支持国医馆的又一代表。
然而,在国医馆运行后,中医界对其的批评逐步增多。主要集中在“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草案”的颁布后,如名中医曾觉叟撰文称,中医以哲学为根本,西医以科学为根本,二者有着较大的区别。中央国医馆本应该维护中医,可是却以科学为中医的主要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医学说的精粹。统一病名建议书主张将西医当作中医病名的标准,以求中医“科学化”更引发了中医们的全盘否定,认为制定者完全为了“科学化”而将中医生硬套入西医概念,是将中医推翻的“恶毒”之举,对中央国医馆越发持消极态度,不予配合。
总结整个中医界对中央国医馆的讨论,不难发现,中医们对于中央国医馆的设立要么抱有国医馆可促进中医“科学化”以更好发展的极大期许,积极学习西医,要么采取较为极端的言辞对“科学化”进行抵抗,排斥西医。可见,此时中西医论争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起初中西医地位平等的相互汇通,到中医与西医的地位出现高低分别,代表科学的西医,已在时代的热潮助推下成为中医汲汲以求或盲目抵制的目标。中医虽时时通过请愿、提案争取着与西医平等的待遇、地位,但实质上,中医的传统愈发松动,日后中医单方面向西医学习的格局自此初步奠定。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米丁一
为你推荐
 资讯
资讯 26省联盟药品集采启动,聚焦妇科用药和造影剂
近日,山西省药械集中招标采购中心发布《关于做好二十六省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品种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开展相关采购数据填报工作。
2025-03-31 21:48
 资讯
资讯 优时比罗泽利昔珠单抗注射液(优迪革)中国获批,全球首个且唯一双亚型创新药治疗全身型重症肌无力
作为唯一人源化、高亲和力且具备创新修饰结构的IgG4单抗,关键Ⅲ期MycarinG试验证实罗泽利昔珠单抗注射液(优迪革®)较安慰剂显著改善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多个临床终点与结局。
2025-03-31 15:58
 资讯
资讯 从手术麻醉到生命全周期护航,麻醉学科发展拓宽生命边界
3月26日,由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等23家学协会共同举办的2025年中国麻醉周学术活动的启动仪式举办,该活动以“生命之重,大医精诚——守生命保驾护...
2025-03-31 15:30
 资讯
资讯 欧狄沃联合逸沃成为中国目前唯一获批的肝细胞癌一线双免疫联合疗法
欧狄沃联合逸沃对比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可显著改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一线患者的总生存期(OS),客观缓解率(ORR)可改善近3倍,中位缓解持续时间(mDOR)达30个月
2025-03-31 13:45
 资讯
资讯 罗氏制药榜首 “现金牛” 产品罗可适(奥瑞利珠单抗)在华获批:开启多发性硬化症一年两次治疗新时代
罗氏制药今日(3月31日)宣布,其旗下创新药罗可适®(Ocrevus®,通用名:奥瑞利珠单抗注射液 ocrelizumab injection)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每六个月静脉输...
2025-03-31 13:39
 资讯
资讯 三生有幸,医者仁心:三生制药向全体医药工作者致敬!
3月30日是国际医师节,由三生制药公益支持的以“三生有幸,医者仁心”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携手20位医生代表,以寄语海报的形式,共同向全体医护人员表达诚挚的祝福与关爱。
2025-03-30 1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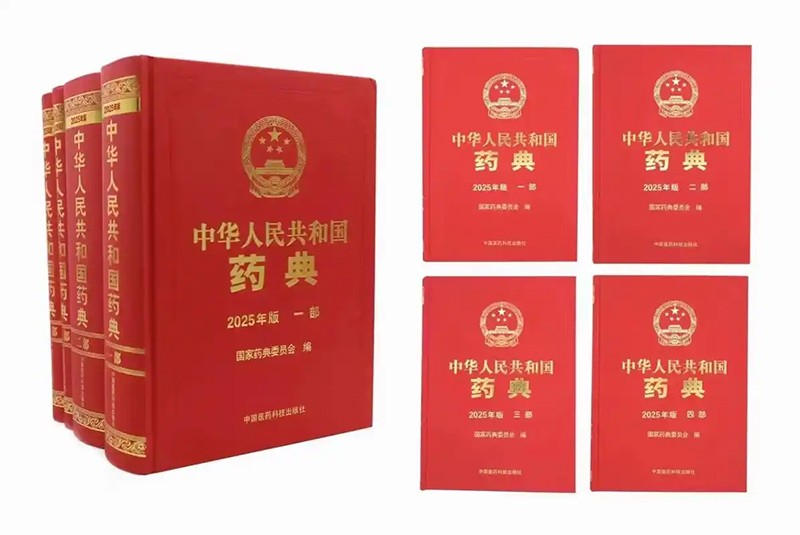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新版药典自2025年10月1日起实施
3月25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国家药监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颁布2025年版的公告(2025年第29号)》,2025年版《中国药典》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
2025-03-30 17:07
 资讯
资讯 向C端发力,华大集团首届健康同行合作伙伴大会圆满举行
3月29日,以“科技普惠,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华大集团首届健康同行合作伙伴大会在华大时空中心成功举办,通过报告演示、展台展示等方式,首次系统性地向外界展示运用生命科学前沿...
2025-03-30 10:38
 资讯
资讯 广州试点创新药械“医保+商保”同步结算
本次试点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在22家试点医院实现医保+商保一站式同步结算,通过提供“商业保险创新药械结算清单”,商保理赔金额将一目了然,市民只需支付医保和商保报销后的...
2025-03-28 1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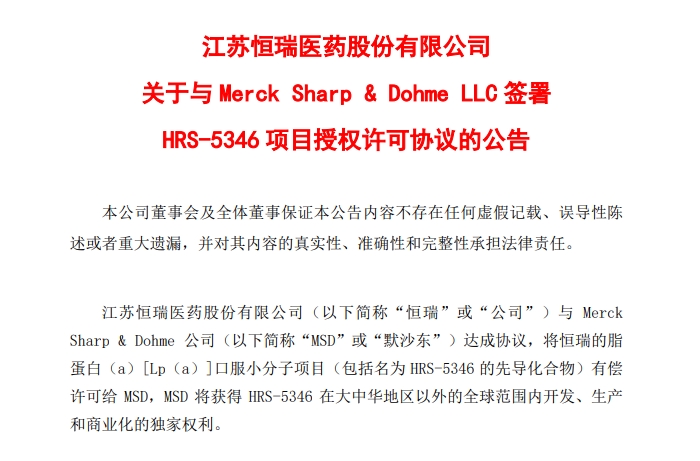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揽入首付款2亿美元,恒瑞医药就一款II期临床药物与默沙东达成新合作
近日,恒瑞医药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默沙东达成协议,将恒瑞医药的脂蛋白(a)[Lp(a)]口服小分子项目(包括名为HRS-5346的先导化合物)有偿许可给默沙东,默沙东将获得HRS-5346在大...
2025-03-28 16:24
 资讯
资讯 国产首款甲状腺眼病靶向药落地湖南,爱尔眼科率先应用
3月27日,爱尔眼科长沙医学中心开出湖南省医院首张国产替妥尤单抗N01注射液处方,并成功为一位中重度甲状腺眼病(TED)患者完成首次注射治疗。
2025-03-27 18:38
 资讯
资讯 复星医药的业绩与生物类似药集采
根据复星医药年报显示,复星医药旗下生物类似药包括第一个国产生物类似药汉利康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汉曲优 、中国首个中欧双GMP认...
2025-03-27 18:21
 资讯
资讯 预购协议被单方面终止,三叶草生物被要求退还2.24亿美元预付款
3月24日,三叶草生物发布公告,称其全资附属子公司三叶草生物制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叶草香港”)收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
2025-03-27 12:10
 资讯
资讯 在华大动作的背后,阿斯利康如何落子“肺健康”
阿斯利康宣布了一项2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北京建立第六个全球战略研发中心,聚焦于肿瘤、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免疫学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前沿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并达成多...
2025-03-27 11:07
 资讯
资讯 罗氏制药与默克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展中国肺癌治疗版图
2025年3月26日,罗氏制药和默克共同宣布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就特泊替尼(拓得康®)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商业化达成合作。双方将充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推动特泊替尼惠及更多METex 1...
2025-03-26 17:17
 资讯
资讯 APASL重磅数据抢先看!吉利德科学公布HBV、HCV、PBC领域多项研究成果
吉利德科学将以壁报和口头报告的形式公布31项肝病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慢性乙型肝炎(CHB)领域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的3期临床研究中国队列随访8年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
2025-03-26 14:19
 资讯
资讯 营收飙涨461%现金储备16亿,云顶新耀2024年成功转型Biopharma
3月26日,港股创新药企云顶新耀(1952 HK)发布2024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公司全年收入达7 06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1%,超额完成了7亿元既定目标。
2025-03-26 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