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做手术到深夜,回家休息了几个小时,早上简单吃了点早餐,又回到医院上班,手上还有几个尿毒症的病人在病房中等着我去查房,观察情况进行下一步治疗。
走进一区病房,几家病人的家属此时正在医院走廊上互相交流着双方的情况,不时感慨着命运的不常,不时相互安慰。
进入病房,立刻印入眼帘的是三个尿毒症病人并排躺在床上,三张浮肿且发出油光的脸与三对呆滞的眼神,拼凑出一幅冷峻而凄楚的画面。这间病房里其中有一个是我的病人,刚从腹膜透析室洗肾回来没有多久,但是血中的尿素氮又快速地升高起来。我量了量他的血压,血压当然也升高了,我不由自主地嘀咕了一句:“指标怎么又增高了呢?奇怪呀。”这让我觉得有些意外,但看了看病人那有些闪躲的眼光和有些愧疚的神情,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是不是偷吃了什么东西?”我带着笑捏捏他浮肿的脚踝问他,一边观察着他脸色的变化。果然他眼睛里透露出一丝慌张,不敢面对我的注视,50几岁、满脸胡茬络腮的大叔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小孩子,那神情和姿态让我忍俊不禁。
我无奈的摇摇头。
很快,过了十来秒钟,神态又恢复到平静的状态,脸色又变回尿毒症患者常有的冷漠厌世的神色,但是我注意到此刻他的眼光已因尿素氮的升高而显得迟钝与混浊。这种情况可不好!我心里暗暗叫到。
我拿起检验科送来的检验单,扫了一眼,看着我的动作,他无奈地摇摇头,瞥了一眼检验科送来的那张似乎普普通通的纸张,苦笑着说:“我偷吃东西你们医生也知道,唉,就算能逃过护士姑娘的眼,也总是逃不过仪器的检查。哎,总是斗不过机器啊。”看着他的这幅模样,我好气又好笑。于是,他坦承在上个星期六,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得了尿毒症,人生也就这样了,天天躺在病床上,闻着医院难闻的消毒水味道,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乐趣可言了,人生乏味,于是趁着女儿和儿子回家休息的空档,找个借口跟护士说自己想出去走一走,活动一下,到公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其实是发下狠心到外面大吃大喝一顿,街边的撸串、大腰子,以前怕不卫生不敢吃,现在自己身体也就这样了,也没有什么不敢吃的了,烤串啤酒一起来,吃个潇洒,混到晚上,然后找个妓女睡觉。第二天早上再悄悄回到医院来,身边的家属和护士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行为,直到检查报告单出来,这些似乎天衣无缝的行为才彻底给暴露出来。
“你们给我的饮食淡而无味,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而且已多快半年没碰过女人了。”他倔着个脸,低声向我抱怨着自己承受的一切。
我了解他所受到的创伤和屈辱。尿毒症病人由于肾脏问题和药物问题,多半会丧失性欲,甚至阳痿,作为一名男性医生,我很能理解他的感受,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他还是一个男人吗?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好像安慰之前很多尿毒症病人一样安慰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尿毒症要严格控制饮食,这些饮食都是为你特设的,只要你能按照医生给你安排的食谱吃,能减少其他系统的并发症。”他还是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让我想到“死猪不怕开水烫”这句话,随着他逐渐沉默下来,我也不再多说话了。
我以为他听过我的话之后,会有些改观,于是放心地走出病房。
但是,没想到,刚结束谈话没多久,当我检查其他病人时,抬起头来,竟然发现他正夹着一块烧烤肉往嘴里送。他看到我在看他,愣了一下子,夹着烧烤肉的手停留在半空中,脸上有些惊异,似乎在惊异我为什么刚离开这么快又回来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无声诉说着他内心的尴尬与纠结,突然一瞬间,他仿佛下了某种决心,有些决然地撇过头去,对手中的那块肉大咬大嚼起来,他宁可饱餐而死,也不愿枵腹而终,我想他一定吃的很痛苦。到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吃的不是美味的烤肉,而是一种对于疾病的绝望,我想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美味。
当他吃完后,我又站在他的面前。他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漠然,用浮肿的手臂擦着油腻的嘴,用他那习惯性无所谓的表情看着我,不过这次眼中多了些挑衅,像个小孩子犯错后对大人的故意挑衅。
我无奈一笑,在医学心理学上,这种行为是典型的病人退化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为像回到小孩子阶段般幼稚。
“你女儿今天怎么没来看你?”查完房,我也暂时没什么紧急的事要忙,于是坐下来跟他聊一聊。
“她去上班了。”他的话很短,像是个闹别扭的孩子,有些倔气。
“想想你的妻子、你的女儿,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会尽量帮助你,你心情要放开朗一点。”我尽量疏导他心中的情绪,搬出他的家人,希望家庭的因素能唤起他对自身的希望。
那次谈话似乎起了一些效果,接着几天,他心情似乎开朗了些,有一天我值班无事,他还专门下床,支开陪床的家人,独自一个人走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谈起他的少年往事,其中还有两则令人艳羡的风流韵事。你可知道,住院这么久,他基本不怎么出病房,每天就待在小小的病房里,无光亮的眼神让人觉得他是在熬日子。我审慎地注意他的神情,一个人若执著于回忆,则表示他怯于前瞻或已不再前瞻。我笑着问他是否再继续偷吃东西,他诡秘地说: “这件事我自有安排。”然后又沉入回忆。看到自己的病人恢复希望,心情转好,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我也乐得听他继续侃大山。
我更告诫过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应严防病人偷吃东西,但这种事,实在防不胜防,而且有损病人的尊严。在适当的治疗下,病人的情况却继续恶化下去,我很替他担心。
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听到模糊的低泣声,仿佛有人在我的心中哭泣,本来是断续的啜泣,最后变为痛声的哀号。我张开眼睛,惨白的天花板格子似乎要压到我的床上来。
我听得出来,最少有五个人跟着一辆推车在楼下的走廊疾速前进。只有人死了,才会发出这种凄厉决绝的哭声,脚步声渐行渐远,哭声亦消失在通往太平间的方向。
外面有月光吗?我在床上翻个身,上弦月就挂在结满蛛网的窗角。如此的月光,照在覆盖死者的白布上该是怎样的颜色?医院的黑夜就像一块铅压在我的身上,然后我逐渐沉入梦乡。
不久,仿佛是那位尿毒症病人的女儿,跌跌撞撞地跑到我床前来:“医生,我爸爸又活过来了,你快去看看!”于是穿着拖鞋的我,急急忙忙跟她越过静寂且有高大油加利树诡异阴影的花园,穿过日本式的长廊,来到开着冷灯的太平间。
死者身上的白布已然拉到胸前,死白并且仍旧浮肿的脸掩映着冷冷的灯光。我靠近病人脸庞,他两个散大的瞳孔正和我做空茫的对视。
“他已经去世了。” 我再度为病人盖上白布,病人的女儿哀苦地说:“医生,请你再看看吧。”
忽然,我的手颤抖了一下,病人的手从白布中伸出来,握住我的手,那是一只多么有力而兴奋的手啊!
然后,我从床上跳起来,天色已经大亮,回想起昨晚做的梦,我感慨一句: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这个不听话又有些可爱的病人,真是让我不省心啊。
早上八点未到,开完交班会,听完昨晚护士做的汇报,我就到病房去。从窗口可以看到那位尿毒症病人正坐在床上用医院送来的早餐,我站在走廊上看着他,又想起昨晚的梦,心里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感觉,然后我走进纷乱的病房中。
“医生,今天这么早就来?”他抬起头,浮肿且有油光的脸正对着从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在阳光中,他的眼睛显得格夕迟钝与混浊。我注意看他的餐盘,他坦然接受我的检视,神情还有些得意,这一次他并没有偷吃在禁止之列的食物。
“昨天晚上有没有溜出去?”我带着笑问他。
“没有,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我想清楚了,这件事我自有安排。”他试图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但嘴角却不太灵光,看起来却像是无声的呜咽。管他呢,只要他想清楚就好。
看向病房窗外,窗外阳光驱散这座城市好几天的雾霾,正贪婪地穿过云层,照在地面上。
医谷链
为你推荐
 资讯
资讯 牵头全国生物药品联盟集采,安徽省医保局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安徽省医保局2025,年,明确开展省级省际药品、耗材集采不少于1个批次;持续推进大型医用设备集采,牵头全国生物药品联盟集采;继续推进慢性病按人头付费机制建设;建立全省统一...
2025-02-23 16:22
 资讯
资讯 药价查询,药价查询,全国已有29个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线定点药店比价小程序
据新闻联播报道,国家医疗保障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线定点药店比价小程序,可实现药品价格在手机上一键查询、实时比对和位...
2025-02-22 2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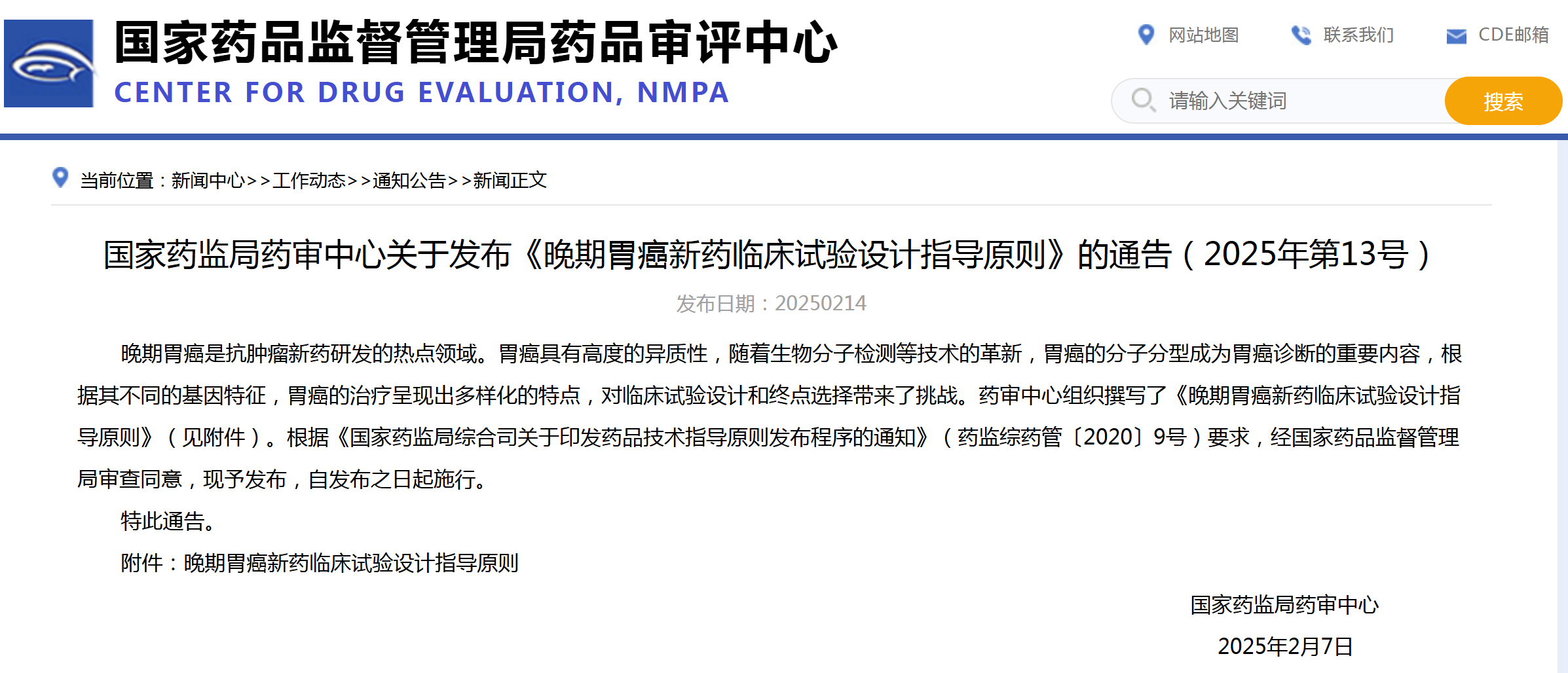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CDE:晚期胃癌新药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
胃癌(Gastric cancer, GC) 是我国高发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其新发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分别位列我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第 5 位和第 3 位。
2025-02-21 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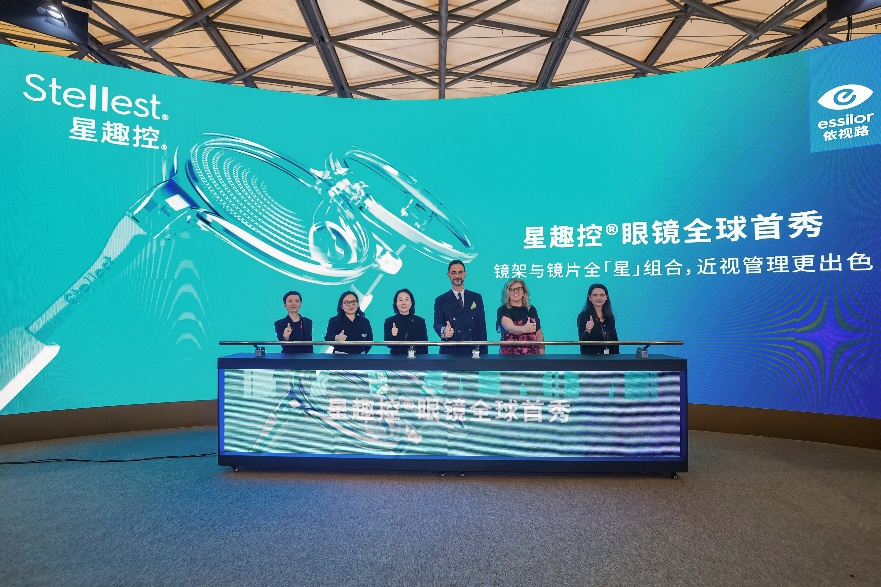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首款依视路星趣控眼镜于上海眼镜展全球首秀 专为近视管理设计 延缓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
依视路星趣控眼镜提供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镜架,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面部结构和尺寸上的显著差异,尺码范围广,覆盖38号至50号,为3-5岁儿童,6-9岁和10-12岁青少年年龄段提...
2025-02-21 17:33
 资讯
资讯 百林科完成A+轮战略融资数亿元,多家投资机构联合投资
百林科成立于2021年9月10日,是一家专注于疫苗、抗体药物、重组蛋白、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血液制品以及其他生物制品关键工艺设备与耗材研发和制造的高科技企业。
2025-02-21 13:30
 资讯
资讯 深研生物完成超3亿元B+轮融资,越秀产业基金领投
深研生物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注于细胞与基因治疗(CGT)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核心技术与设备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2025-02-21 13:23
 资讯
资讯 阿斯利康以1.6亿美元收购珐博进中国,获得罗沙司他在中国的独家权利
昨日(2月20日)晚间,阿斯利康在其官微宣布与珐博进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将以约1 6亿美元收购珐博进中国。
2025-02-21 10:20
 资讯
资讯 快速崛起的中国创新药公司,真实生物赴港IPO
2月18日据港交所披露,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实生物“)递交上市申请书,中金公司为其独家保荐人。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生物科技企业,以创新药物研发为核心,专注于...
2025-02-20 20:57
 资讯
资讯 华东医药经皮肾小球滤过率测量设备获批,有望提供GFR监测新方法
2025年2月19日晚,华东医药(000963 SZ)公告,其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申报的创新产品三类医疗器械经皮肾小球滤过率测量设备注册申请获得上市批准。
2025-02-19 19:15
 资讯
资讯 国采中选企业满足一定条件,可变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及生产企业、增加规格包装等,第一批名单发布
2月18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部分中选药品信息变更的通知(第一批)》,涉及到5批国采的15个品种。
2025-02-19 18:26
 资讯
资讯 凯米生物完成超亿元Pre-A轮融资首关,加速肿瘤治疗性疫苗全球布局
此次融资将用于加速核心产品SN3001(前列腺癌治疗性疫苗)、SN2001(慢性乙肝免疫治疗疫苗)的全球临床,以及基于SynNeogen®核心技术平台的肿瘤治疗性疫苗产品持续布局。
2025-02-19 13:50
 资讯
资讯 潜在交易金额超12亿美元,石药集团ADC癌症新药达成国际授权合作
今日(2月19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其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Radiance Biopharma达成协议,Radiance Biopharma将获得巨石生物自主研发的重组抗人类受体酪氨酸激酶样孤儿受体1...
2025-02-19 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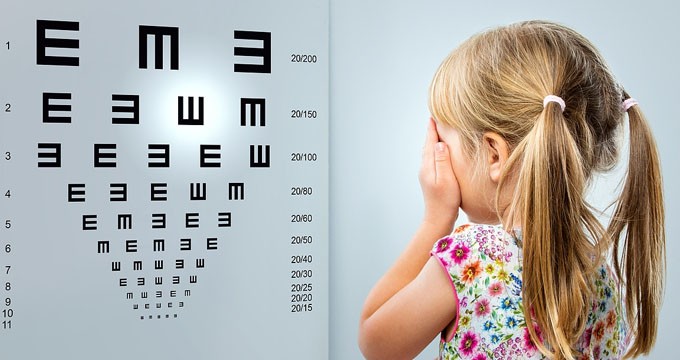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又一玩家加入,来自恒瑞医药的“近视神药”上市申请获受理
近日,恒瑞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公司已经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旗下产品 HR19034滴眼液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
2025-02-19 10:47
 资讯
资讯 国家医保局:医保领域2025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
2025年底前,全国80%左右统区基本实现与定点医药机构即时结算。基本实现医保部门与医药企业对集采药品的直接结算,加快推动与医药企业对集采医用耗材、国谈药的直接结算。
2025-02-18 21:14
 资讯
资讯 “悦如初,达新程” 2025特应性皮炎免疫创新学术会议于成都举办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在非致命性皮肤疾病中疾病负担位列第一,给患者个人及家庭带来沉重的生理、心理负担,造成长期的社会影响。
2025-02-18 10:58
 资讯
资讯 拜耳在欧盟申请EyleaTM 8mg治疗间隔延长至6个月
拜耳已向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提交申请,将EyleaTM 8mg(阿柏西普8mg,114 3mg ml注射液)用于治疗两种主要视网膜疾病,即新生血管(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和糖...
2025-02-17 19:55
 资讯
资讯 EyleaTM 8mg延长给药间隔治疗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在三年时得到证实
近日,在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第22届新生血管年会上,拜耳及其合作伙伴Regeneron公布了PULSAR开放标签扩展研究治疗新生血管(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患者第三年的临床试验结果。
2025-02-17 19:44
 资讯
资讯 备思复(维恩妥尤单抗)联合疗法全国首张处方落地,开启泌尿肿瘤精准治疗新篇章
2025年2月17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泌尿肿瘤暨黑色素瘤肉瘤内科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军教授为一位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开具备思复(维恩妥尤单抗)联合帕博利珠...
2025-02-17 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