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实行七年之后,怨声载道的医保总额预付制度即将退出。
2月26日召开的2016年上海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传出消息,要逐步强化按病种、按人头付费等方式,逐步淡出“医保总额预付”制度,解决医院因为怕医保总额超标,从而不愿意进、不愿意开高价医保药物的问题。
做法变形的争议制度
上海是人社系统最早开展医保总额预付的七省市之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总额预付的基础上,上海2009年在三家综合性三甲医院启动首批总额预付试点,次年试点医院扩大至10家,并于2011年起在全市所有二、三级医疗机构全面实施。
总额预付是一种操作非常简便的医保控费制度:根据上年度基金使用情况,加上一个合理的增长率,作为医疗机构一年的报销总盘子,医保花费因此有了上限。2010年,在病人数量增长10%的前提下,上海的药品费用增速从往年的10%降至3%-4%。
仁济医院着名的泌尿外科,一年7500台手术,占全院手术量的25%。实施医保总额预算第一年后,住院均次费用下降了11%,均次药费下降了5%。
但在实施过程中,总额预付的弊端也开始显露:一旦额度紧张,推诿病人就成为最简单的办法。每年1-3月是上海医保年度的末季,也是推诿病人的高发期。而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考核指标,对此并拿不出有效的办法。
“挑选病情不那么严重的病人,一样可以完成工作量”,长期研究上海医改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胡苏云曾直言,这样一来重病号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更为诱惑的是,收治病情较轻的病人,可以加快病床周转率,一方面缩短了“平均住院日”这一对三级医院考核严格的指标,另一方面增加了医院的经济效益。
推诿病人最极端的案例,当属2012年2月底,上海市民秦岭患肺癌晚期的父亲被多家医院推来推去、两个月内被迫辗转五家医院,不得不给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信。
随后当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教授即通过媒体,直陈总额预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层层分解指标的根本性危险——医保指标的逐级分解,在一定程度上把住院统筹基金分解成了个人账户模式,从而消解了医保统筹基金的共济和风险分散功能,制度运行的脆弱性骤然增大,这种看似精确的做法无异于釜底抽薪。
两大行政系统的微妙博弈
作为中国一线城市,上海现行的医保制度中新农合的体量几可忽略不计,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都由人社部门管理;而使用医保基金的医疗机构隶属卫生行政部门,医保基金的实际运作牵涉到两大系统,往往磨合不畅。
上海人社系统曾经的部署是,从相对粗放但也容易实施的医保总额预付制度入手,同时研究精细化的控费模型、乃至更为有效的控费方式比如按病种付费(DRGs);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医保角色的转型,从单纯的控费逐步接手药品乃至耗材的招标,力图充分发挥“支付方”的功能。
但人社系统的医保根本无法有效监管强势的三甲医院。反过来,随着总额预付制度的推进,医疗机构方面也是啧有怨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有关人士发表学术论文称,总额预付的制度基础是定点医疗,而上海实行参保人员自由就医政策,使得总额预付成为“无本之木”,基金预算缺乏科学依据。
此次上海提出要强化按病种和按人头付费等医保支付方式,其中按病种付费的基础是临床路径,而各学科临床路径的制订是由卫计委系统召集的医疗专家负责;按人头付费主要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签约模式,服务内容也主要由卫计委来制订。可以说,总额预付制度的淡出,意味着卫计委加强了在医保管理方面的话语权。
不过,正如朱恒鹏曾指出,目前我们推行医保总额预付制度尚缺乏基础,它不适宜在医院层面实施,世界各地也没有这样的先例——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都是在地区层面做的总额预付,美国是在老兵退伍医院搞,而老兵退伍医院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一家医院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医联体。
来源:医学界智库 作者:李草凡
为你推荐
 资讯
资讯 默克全球执行副总裁周虹:合作与创新是默克未来五年战略的两大关键词
近日,德国默克医药健康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及国际市场负责人周虹带领医药健康中国及国际市场管理团队开启了2025年度首次“中国行”。
2025-04-01 17:11
 资讯
资讯 首个且唯一,阿斯利康PD-L1单抗获FDA批准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作为新辅助治疗,随后度伐利尤单抗作为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的辅助单药治疗,用于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成年患者。
2025-04-01 1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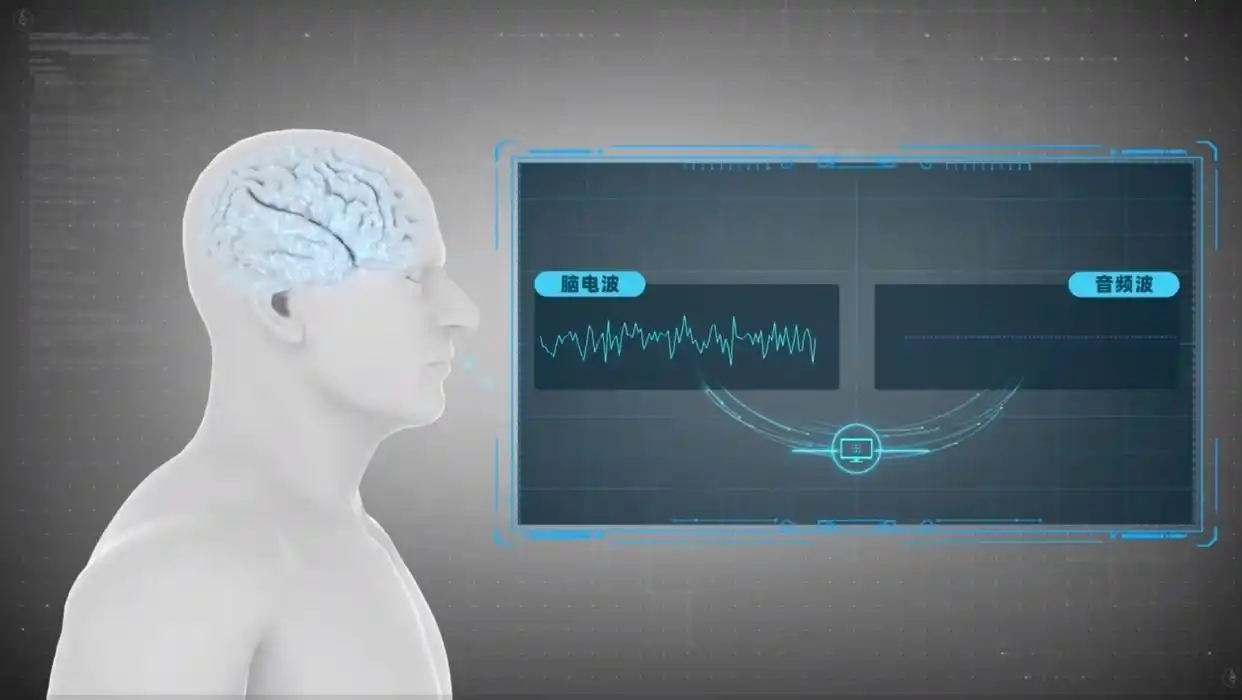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全国首个,湖北为脑机接口医疗服务定价
昨日(3月31日),据“湖北发布”消息,湖北省医保局发布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医疗服务价格,其中,侵入式脑机接口置入费6552元 次,侵入式脑机接口取出费3139元 次,非侵入式脑机...
2025-04-01 11:03
 资讯
资讯 一款国产创新流感药,获批
近日,据国家药监局官网信息显示,青峰医药下属子公司江西科睿药自主研发的1类创新药玛舒拉沙韦片(商品名:伊速达)正式获批上市,用于既往健康的12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单纯性...
2025-04-01 10:22
 资讯
资讯 26省联盟药品集采启动,聚焦妇科用药和造影剂
近日,山西省药械集中招标采购中心发布《关于做好二十六省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品种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开展相关采购数据填报工作。
2025-03-31 21:48
 资讯
资讯 优时比罗泽利昔珠单抗注射液(优迪革)中国获批,全球首个且唯一双亚型创新药治疗全身型重症肌无力
作为唯一人源化、高亲和力且具备创新修饰结构的IgG4单抗,关键Ⅲ期MycarinG试验证实罗泽利昔珠单抗注射液(优迪革®)较安慰剂显著改善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多个临床终点与结局。
2025-03-31 15:58
 资讯
资讯 从手术麻醉到生命全周期护航,麻醉学科发展拓宽生命边界
3月26日,由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等23家学协会共同举办的2025年中国麻醉周学术活动的启动仪式举办,该活动以“生命之重,大医精诚——守生命保驾护...
2025-03-31 15:30
 资讯
资讯 欧狄沃联合逸沃成为中国目前唯一获批的肝细胞癌一线双免疫联合疗法
欧狄沃联合逸沃对比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可显著改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一线患者的总生存期(OS),客观缓解率(ORR)可改善近3倍,中位缓解持续时间(mDOR)达30个月
2025-03-31 13:45
 资讯
资讯 罗氏制药榜首 “现金牛” 产品罗可适(奥瑞利珠单抗)在华获批:开启多发性硬化症一年两次治疗新时代
罗氏制药今日(3月31日)宣布,其旗下创新药罗可适®(Ocrevus®,通用名:奥瑞利珠单抗注射液 ocrelizumab injection)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每六个月静脉输...
2025-03-31 13:39
 资讯
资讯 三生有幸,医者仁心:三生制药向全体医药工作者致敬!
3月30日是国际医师节,由三生制药公益支持的以“三生有幸,医者仁心”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携手20位医生代表,以寄语海报的形式,共同向全体医护人员表达诚挚的祝福与关爱。
2025-03-30 1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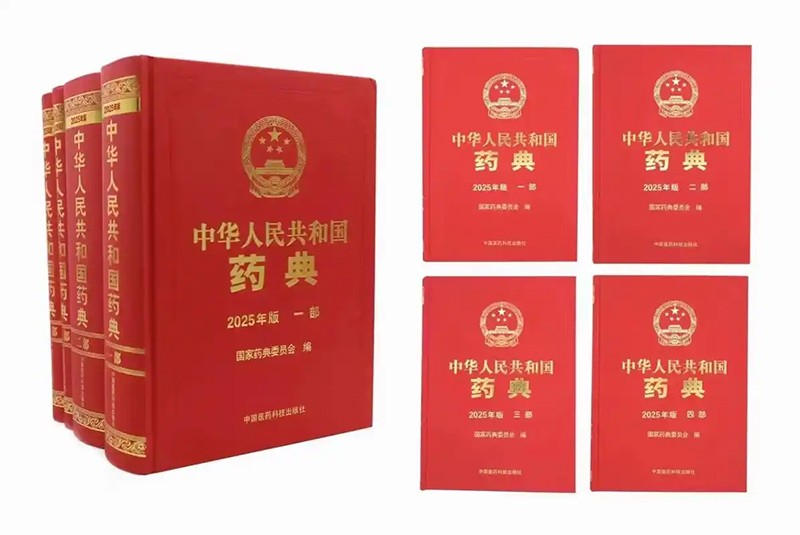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新版药典自2025年10月1日起实施
3月25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国家药监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颁布2025年版的公告(2025年第29号)》,2025年版《中国药典》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
2025-03-30 17:07
 资讯
资讯 向C端发力,华大集团首届健康同行合作伙伴大会圆满举行
3月29日,以“科技普惠,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华大集团首届健康同行合作伙伴大会在华大时空中心成功举办,通过报告演示、展台展示等方式,首次系统性地向外界展示运用生命科学前沿...
2025-03-30 10:38
 资讯
资讯 广州试点创新药械“医保+商保”同步结算
本次试点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在22家试点医院实现医保+商保一站式同步结算,通过提供“商业保险创新药械结算清单”,商保理赔金额将一目了然,市民只需支付医保和商保报销后的...
2025-03-28 1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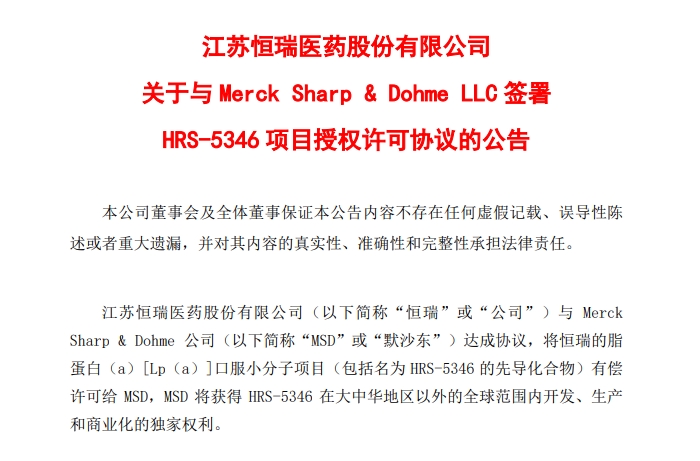 资讯
资讯 揽入首付款2亿美元,恒瑞医药就一款II期临床药物与默沙东达成新合作
近日,恒瑞医药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默沙东达成协议,将恒瑞医药的脂蛋白(a)[Lp(a)]口服小分子项目(包括名为HRS-5346的先导化合物)有偿许可给默沙东,默沙东将获得HRS-5346在大...
2025-03-28 16:24
 资讯
资讯 国产首款甲状腺眼病靶向药落地湖南,爱尔眼科率先应用
3月27日,爱尔眼科长沙医学中心开出湖南省医院首张国产替妥尤单抗N01注射液处方,并成功为一位中重度甲状腺眼病(TED)患者完成首次注射治疗。
2025-03-27 18:38
 资讯
资讯 复星医药的业绩与生物类似药集采
根据复星医药年报显示,复星医药旗下生物类似药包括第一个国产生物类似药汉利康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汉曲优 、中国首个中欧双GMP认...
2025-03-27 18:21





